城镇化是个古老的话题,有关城镇化问题的讨论,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后随着现代城市的产生,就开始出现了,在230年前亚当·斯密伟大的著作《国富论》中,就有有关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关系的讨论。但显而易见,在每个时期,城镇化会成为理论与政策的讨论中心,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都有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
近几年来,城镇化能成为中国政府与中国理论界讨论的中心问题,显然是与2007年爆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紧密相关。回顾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特别是新全球化展开以来的这二十年,中国经济能够出现持续的高增长,是建立在外需高度扩张的基础上,由此形成了外向型的供给和需求结构。有关分析说明,至少在新千年以来,中国的生产和投资,有一半以上是与出口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这种情况在2007年达到了高峰,当年净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8.8%,而2000年只有2.4%。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中国外需增长过程中断。开始时许多人认为,次贷危机与以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没有什么不同,是周期性的波动,因此中国的外需很快就可以恢复,但是在危机已经爆发六年后的今天,大部分人的想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这场危机的特殊性开始被世人所认识,危机将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观点开始成为主流认识。随着发达国家为摆脱危机而不断实施了走向极端的货币政策,关于可能会爆发更大规模的货币金融危机的讨论也多了起来。若外部危机绵延不绝,中国的外需就难以恢复,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回到以往依靠外需拉动的轨道。
所以在危机爆发后,特别是近三年,关于必须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讨论逐渐热烈,怎样从外需转向内需,内需的拓展重点应怎样选择,是必然要涉及的问题,而城镇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走入了理论与政策的中心领地。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城镇化会成为拓展内需的主要方向呢?简单地说,工业化所创造的供给,是为满足城市人的需求发生的,所以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可分割。但是改革前30年和改革后这30年中,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使中国采取了“城乡分割”的发展方式。“城乡分割”在改革前的30年,使中国得以快速发展起一个足以自立的重工业,但是却积累了庞大的农村剩余人口。改革开放这30年,虽然通过“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办法,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农村人口工业化的问题,却还没有解决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问题。在今天反思新中国60年来的发展历程,这种抑制城镇化的战略取向虽然有其历史功绩,但发展到今天弊端也暴露无遗,就是由于保持了庞大的低收入农村人口,使国内的需求与供给规模严重不对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外需的严重萎缩,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突出出来。当然,国内分配体制矛盾对当前的过剩格局也有着重大影响,但是大量研究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在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中居于主体地位。因此,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可以产生巨大的内需。
还要看到,大幅度提高城镇化率,以使得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相称,不仅仅是具有拓展内需的作用。试想,即便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进入到发达国家水平,可是真实的城镇化率按照目前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才刚刚超过50%,中国能算是一个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吗?
另一方面,城乡结构扭曲属于大结构的扭曲,不从根本上解决大结构扭曲的矛盾,不仅会使工业生产由于过剩矛盾难以继续发展,也严重阻碍着农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步伐。
从农业看,大量农民工虽然已经进城打工,但是仍长期保留着对家乡土地的经营权,使中国的耕地不能实现集中经营,即便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空村”,即便已经造成了上千万亩土地的抛荒,仍不能实现土地集中。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是实现农业机械化,土地长期归小农户所有而不能集中,就是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阻碍。近年来,由于出现了“民工荒”,学界在热烈讨论所谓“刘易斯转折点”的问题,但是如果看到美国仅以200多万农业劳动力就养活了3亿美国人,还出口了占世界出口量60%的粗粮,而中国直到2012年却仍然有2.58亿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只是被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所掩盖的一个假象。只要在土地规模经营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就会有超过两亿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所以,通过大规模的城镇化使8亿农民进城,从而彻底脱离与农村土地的关系,是使中国农业最终走向现代化的必须条件,并且也只有建立了现代农业,中国才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从服务业看,大量低收入农村人口的长期存在,是压低服务业增长空间的最大因素,因为组成现代服务业的许多商业机构,都不可能在分散的农村发展,进城打工的农民,由于在城市没有家,也不可能产生像城市人那样的服务业需求,所以尽管目前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已经高达3倍以上,而像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的城乡消费差距,更高达4-5倍,并且使中国与同等人均收入国家的服务产业比重相比,要低15-20个百分点。所以,也只有使大量农民工携家带口进城,转换成市民身份,才会有服务业的巨大增长空间,才能使中国服务产业的比重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匹配。
因此,未来20年城镇化是个“纲”,抓住这个“纲”,才能做到“纲举目张”,使中国的三次产业格局彻底摆脱大结构扭曲的矛盾,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各种发展战略的制定也好,只有围绕这个“纲”来设计和实施,才会见到显著效果。
按照新千年前十年的情况计算,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的增长速度,需要每年新增8万亿元左右的新需求,大体是出口和消费各2万亿元,投资新增4万亿元。新千年以来,中国新增真实城市人口约1亿人,同期新增的城镇投资约50万亿元,大体上是每新增1个城市人口,会吸纳50万元投资。如果未来20年中国新增城市人口达到8亿人,所能产生的投资需求就是40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这已经大大超过了“保9”所需的社会总需求年均增长额。如果把服务产业的发展空间拓展到占经济总产出的60%,也可以在未来20年提供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这就是结构转换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道理。由此而言,所谓中国经济将转入“中速增长”甚至“低速增长”的那些预言,根本是站不住脚的。由于城镇化把大量农村人口吸纳到城市,使中国农业得以完成现代化改造,可以新增数以亿计的新增非农劳动力,所谓中国经济将丧失国际比较优势的预言,也都早晚会让人们觉得不值一驳。而中国将长达半个世纪的持续高增长,在完成城镇化的凯歌中,才会被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改革开放这30年,不管是体制还是战略,中国都是在摸索中从模糊到清晰,城镇化战略也会是如此。目前我们虽然对城镇化战略的大方向已经有了把握,但是还是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甚至仍然有较多争论。比如,城镇化的重点是应该放在大都市圈、城市群方面,还是应放在小城市与城镇?农民工在转变成市民的过程中,社会保险、住房等问题应怎样解决?在变成市民后,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应通过怎样的制度安排,实现集中与规模经营?由于未来20年可能有8亿农民要进城,是现有城市的近两倍,中国一定会出现许多新城市,许多现有的城市规模也会显著扩大,这些新城市、大城市和城市群将诞生在哪里?为农民进城必须兴建大批政策性住房,需要占用大量城市土地,现有的“土地财政”将走向尽头,而若没有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城镇化就很难推动,因此新的财政体制应该怎样设计?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的城镇化未来需要数百万亿元资金来完成,这些资金应怎样筹集?特别是在启动城镇化的初始时期,怎样才能筹集几万乃至几十万亿元的启动资金?这些问题不解决,城镇化或是难以启动,或是要“打乱仗”。由于城市是公共产品,主导未来中国城镇化高潮的肯定应当是政府,而不是市场,所以城镇化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比以往向市场放权的时代更高的要求。
热搜品推荐:
中联ZE360E挖掘机
三一SF808电液压桩机
中联44米混凝土泵车
福田雷沃重工FR622D旋挖钻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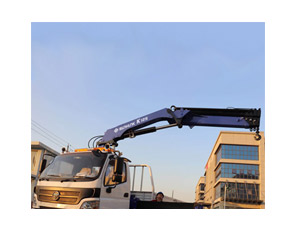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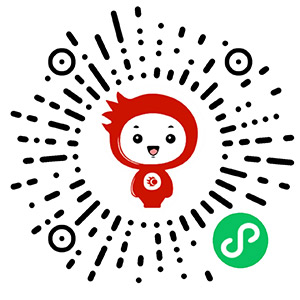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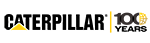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