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决定》的发布和实施,意味着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用官方的提法叫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这一轮改革,如果要全面执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绕不过的坎儿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国有企业不仅是市场和政府边界最模糊的地方,也是时下市场和政府之间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和暴露的地方,市场基础性作用提出20多年来效果难以充分发挥与此关系极大。经济体制改革在若干领域的重点攻坚若想取得突破,均需要跨越国企改革这道坎,如要素市场化、打破垄断、平等市场准入、财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等,都与国企改革息息相关。
事实上,2003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驱动力,除了“入世”红利,另一个就是90年代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给市场带来的空间,以及这种空间创造出来的经济活力,突出表现在非国有经济远超国有企业的规模增长和资本回报。过去30年,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在营业收入和增加值上的增幅比国有工业企业要分别高出40和20个百分点,这是非国有经济占工业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20%上升到2010年的73%的主要原因。
目前国企改革面临的问题并非改善公司治理、提高盈利能力及利润上缴比例(20%还是30%)等国企本身的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重新定位国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
首先,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电力、煤炭、铁路、航空、金融等要素和基础行业领域长期占据垄断地位,并利用这种垄断获得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掩盖了其效率低下和长期存在的负盈利能力问题。国企无法退出加剧产能过剩,2000年国家经贸委就认定钢铁产能过剩,但随后新增产能不断上升,地方给予的土地、资金、水电费优惠一如既往。而市场的另一头—效率很高、嗷嗷待哺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无法公平地获得生产要素和准入机会,且饱受资源、要素被长期滥用和错配产生的通胀之苦。国有企业已成为扭曲全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源头,使全社会资源配置离真正的市场化渐行渐远。
其次,国有企业改革踌躇不前是政府职能无法转变的主要障碍。国有企业关系着地方经济增长、税收、就业和社会稳定,也关系着地方要员的政治前景。集多种诉求于一身,国有企业在不能改变经营低效的情况下,做大成了维护各方利益的唯一选择,这便将国有企业和政府捆绑得越来越紧,产生了“大而不倒”、道德风险盛行的现象,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愈加模糊。于是,国有企业存在困难的时候,政府帮助其渡过难关(如靠上新产能来解决过剩产能、游说银行不追债、帮企业缴罚款等)便是公开的现象、不得已的选择,政府介入市场越来越深,而其职能转变也就流于空谈。
再次,国企使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难以建立。在中国,稍具规模的国有企业就很难通过破产来退出,即使是僵尸企业也往往通过兼并、收购等形式来获得暂时的安宁,它不仅拖垮了效益较好的企业,而且将问题掩盖和延后。国企这种“不管天下如何乱我自安然”的超稳定景象,破坏了正常市场交易和竞争机制。不仅国企靠政策优惠和垄断,很多为国企做配件或边缘业务的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也通过关系笼络来获得市场订单和份额,甚至在华外企也如法炮制,整个市场秩序非常混乱,各种无序的、不公正的竞争手段非常流行,而统一、竞争和有序的市场体系和规则无法形成。
最后,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制约了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在国有企业和政府双重陷入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谁都无心在技术改造、科技创新上下功夫。打着技术改造或科技创新的幌子,骗取政府土地、税收优惠、财政贴息的企业有的是,变相搞房地产的也很多。例如,光伏行业红红火火了几年,但盛极的景象下面难掩制造业的本相,而政府让国有企业来接管烂摊子(无锡市让国联接管尚德电力)、银行坏账纳入财政预算(新余市将赛维债务纳入政府预算),更是让政府追逐的是GDP政绩而非产业升级的用心大白于天下。
国有企业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中,为完善国民经济体系和提升国力上发挥过一定作用。在1990年代中期市场化改革中,国企退出制造业竞争性领域,转向扮演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者(如道路交通、港口、电站等),以及资源“拓荒者”(如电信、煤田、油田和水利等的建设)等角色。在市场主体力量不强或不愿进入的情况下,确实需要国企先期进入,培育和构建市场运行所需的有形或无形基础设施。等到市场成长了、基础设施完善了,这时国有企业就应该退出,转向市场运作所必需的新的基础设施的需求,如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下网络基础设施的全覆盖和维护、金融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城市中心与外围公共服务均等化、住房保障),同时为补充社保欠账作贡献,而国企对市场不愿进入的新领域(如探月工程、生物医药领域前期研发等)的培育也可归类在此。国有企业如果以此为定位,就基本上厘清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者单位: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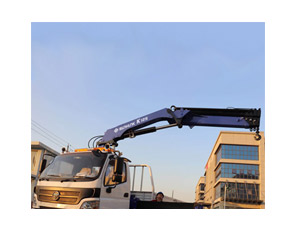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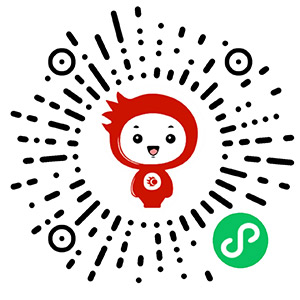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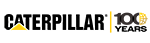
























热门推荐